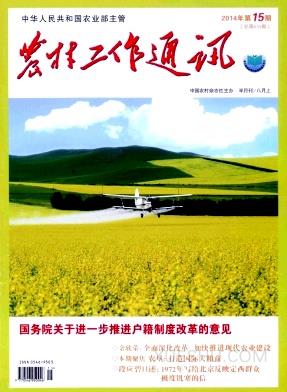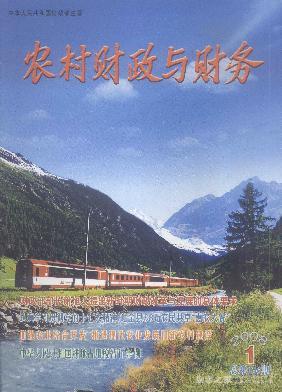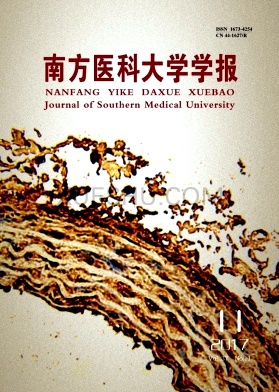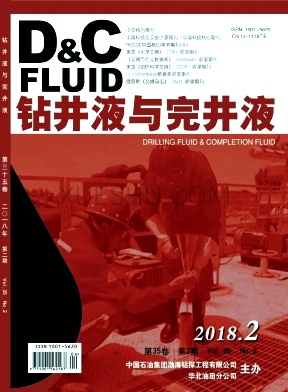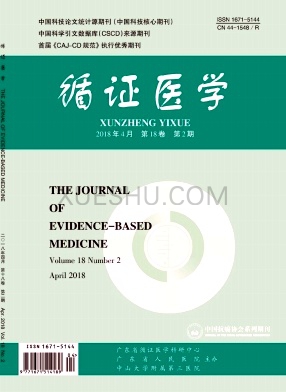试论太宰治文学前期到中期的转变
太宰治的文学创作风格在中期发生了重大转变,通过对其一贯的文学基调与中期转变原因的分析,可以窥见中期的文学特质依然如故。在中期作品健康、明快的色彩下面,涌动着虚无、反叛与自我否定的暗流。
关键词:表象;两面性;文学基调
1、太宰治的文学创作生涯通常被划分为三个时期,前期是其自称为“排除与反抗”的时代(1932—1937),这一阶段的作品大多格调灰暗,带有较强的颓废色彩,主要描述了作者在青春时期的苦恼与不安。中期是所谓“安定与开花”的时期(1938—1945),这段时间的作品与前期明显不同,文风健康、明快,作品主题也大都乐观、向上。后期是太宰治被称作“新戏作派”作家的战后三年(1945—1948),此时的作品再度呈现出虚无与颓废的特点,与前期文学有着相似之处。 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而同一作家不同时期的风格与表现手法也会有所差异。但太宰治前期到中期作品风格的转变之大在其他作家身上尚不多见。这种转变始于1938年发表的《满愿》,随后推出的《富岳百景》、《新树之语》、《奔跑吧!梅洛斯》等,也不断地展示了其创作上新的倾向。评论家们认为新的文风“明快、平和” (奥野健男)、“健康、达观,充满了对人生的温暖的热爱”(龟井胜一郎)、“慰藉心灵的路旁之花”(丰岛与志雄)(1)。在这些新作里,很难再看到前期的语言表达上的晦涩、思维的近乎错乱、充满激情的宣泄。从作品的表现手法上看,前期的《晚年》、《虚构的彷徨》、《二十世纪旗手》等作品属于大胆的实验性的前卫小说,而中期的《富岳百景》、《奔跑吧!梅洛斯》等名作中体现出的是在 艺术 表达上近乎完美的水准与境界。那么,前期与中期之间在风格上如此之大的转变,是如何发生又具有什么样的背景与原因呢?本文将对上述问题谈谈笔者的看法。
2、1932年,决心投身文学事业的太宰治开始创作《回忆》。这部处女作是作为“我幼年及少年时代的告白”(2)而写成的,它叙述了太宰治因深深的自卑而产生的苦恼、要强于他人的贵族意识、为掩饰被家人及同学排斥而强作出来的幽默、对弱者的同情、深藏于内心的宿命观等。而此后的前期作品也大多具有这样的风格,作品中的人物大多是作者本人思想的代言人,诉说其对青春时期丧失自我和否定自我的彷徨、对世俗进行的叛逆和反击。
奥野健男在《太宰治论》中指出,太宰治前期作品的基调是一种“反定立的精神”。正是从这种叛逆意识中,作者产生了前期的虚无颓废与自我否定。可以说,太宰治的文学精神(反叛意识与自我否定)萌芽于他特殊的身世与青春时期的经历。其中,在津轻的风土中长大、出身于名门、身处家中第六子的尴尬地位这三大要素,使太宰治从少年时起就具有了与生俱来的贵族意识与自卑感。这一复杂又矛盾的性格特征也 自然 影响到了他的创作生涯,而从其性格中产生的面对现实时的叛逆与自我否定也成为其文学创作的主要基调。
1937年起,太宰治经历了一年半左右的沉默时期。但是,于次年复出的他却以不同的形象再现于文坛。他发表了数篇完全不同于前期风格的作品,并自此步入了“安定与开花”的创作高峰期,推出了许多健康、明快的佳作。其中,《奔跑吧!梅洛斯》还被选入了日本初中的国语教科书。那么,他的文学创作风格发生如此巨大变化原因是什么呢?
3、奥野健男认为中期转变的原因有二:一是太宰治因镇痛剂中毒被送入精神病院事件,二是住院期间妻子与别人私通。关于这两件事,在太宰治的自传式作品《东京八景》中已有详细说明,它们作为其中期转变的重要原因,已获得了学界的认同。此外,鹤谷健三认为,太宰治对自己以往的文学表现手法的怀疑也是其转变的一个重要原因。1935年,太宰治凭作品《逆行》入选“芥川文学奖”候补,但结果石川达三的《苍氓》获得第一名,太宰治仅居次席。自负的他觉得自己受到了莫大的侮辱,并在1937年发表的《地球图》序言中表示不满,认为自己受到了不公的冷遇,作品未得到应有的评价。关于创作手法,他认为自己以往的作品过于雅致,未曾为迎合读者而作过通俗的说明与加工。但在现实中,这种真正的艺术作品却犹如对牛弹琴。于是,他对前期前卫式的文学表现方法开始表示怀疑,并试图进行改变。 除了上述三点原因以外,笔者认为当时的外部环境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要素。从时代背景来看,1937年正值日本全面侵华的开始。在战争期间,政府对文化的干涉与管制也随着同年7月爆发的“卢沟桥事变”愈演愈烈。当局极力鼓吹“国策文学”,这使得讴歌军国主义的御用文人得到重用,而不利于战争宣传的文学作品却受到打压。如作家岛木健作的《再建》与石川达三的《活着的士兵》在当时都被政府禁止发行。在这种言论管制、思想镇压的大环境下,只有少数作家巧妙地避开 政治 上的敏感地带,进行了纯 艺术 上的创作,从而使自己的文学生命得以继续。太宰治此前的作品由于大多格调灰暗,充斥着自我否定、自我破坏的内容,这当然不符合军国主义政府进行战争宣传的要求。因此,他只得与其他少数作家一样,要么改变风格取材,要么终止文学创作。于是,太宰治创作了一系列不同于前期的作品,如讴歌诚实和信用的《奔跑吧!梅洛斯》、健康清新的《满愿》、取材自 中国 古典文学的《清贫谈》、《御伽草纸》等。所以客观地说,战争时期的文艺政策在客观上对于太宰治文学生涯的 发展 起到了积极作用。
综上所述,太宰治在中期文学风格上的变化,可以说是被动与消极的。一个作家的作品风格及表现手法的转变并不意味着其文学精神也一定会转变。笔者以为,太宰治特殊的身世与成长的经历,促使其文学基调在创作生涯的前期即已形成。尽管上述的四个原因促成了他在中期文学风格上的巨大变化,但这是被迫完成的,中期的“健康、明快”只是一个表象。实际上太宰治是以新的风格隐藏了真实的自我,这个仍旧消极、虚无的自我才是他的本质。并且,中期文学的两面性(自我肯定与自我否定、理想主义与虚无主义、对人的信赖与怀疑等)在《满愿》、《富岳百景》、《奔跑吧!梅洛斯》等代表作品中有着明显的体现。二战后,步入文学生涯后期的太宰治所创作的一系列著名作品中,再次出现了否定自我、颓废、悲观的倾向,这也是他一贯的文学精神的复活。许多日本的文学评论家都称中期为“安定与开花”的时代,但似乎对中期作品的本质揭示得不够。太宰治的出身与成长环境、其文学基调在前期的形成以及促成其中期作品风格转变的四个原因,才是解读中期文学特质的重要前提,这些对于考察中期作品中的的两面性是极其关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