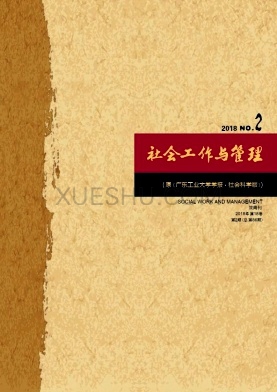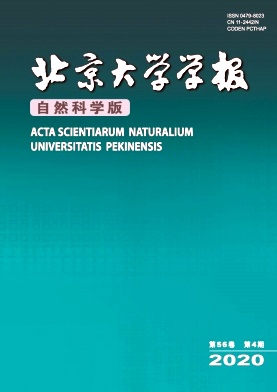试论性别的建构——基于河北省H村就业市场的研究
河北省H村存在着男女两个不同的就业市场,这种就业市场是社会性别机制及其背后的社会文化造成的,它既与宏观的就业制度和政策有关,又与家庭男权话语及将两者内化的妇女自我意识有关,是社会性别建构的结果。
论文关键词:性别;女性;就业市场
周颜玲指出,学界对性别关系的研究已经从强调个人的“地位”和“角色”的社会性别观转变到强调结构、制度的层面,学者们从劳动分工、政治权力等多方面分析社会性别的结构因素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对就业市场而言,康奈尔构建了三重的性别结构模型,其中在生产关系方面认为性别的社会分工是常见的,在当代的条件下并不必然体现为明确的歧视,而是存在于复杂的机制中。Yodanis通过对大西洋一些岛屿捕鱼业的研究发现,捕鱼业中的性别隔离是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在渔猎社区,男人被定义为捕鱼者,妇女被定义为“非捕鱼者”,即使她们在渔船上工作时都是如此。这使妇女们不能参与到村庄最有利可图的工业中,因此职业的性别隔离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容易消除。潘振飞在《当前农村已婚妇女外出就业动因的社会人类学分析》一文中,运用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认为,农村妇女外出就业是社会宏观、微观结构和主体两个层面相互作用的结果。上述文献实际指出,性别的职业隔离不是单一的性别角色所能解释的,它是社会制度、政策等结构因素与性别主体共同促成的,两方面结合在一起形成性别隔离的就业市场,而这种局面又在日常生活中不断生产和再生产,由此形成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规范。
基于上述文献,本文运用深入访谈、问卷调查、参与观察等方法对河北省H村就业市场中的性别状况进行了深入研究,以探讨就业市场中的结构性因素及女性主体意识。笔者于2005年7月、12月和2007年8月三次到H村。H村位于河北省北部,人口726人,232户,劳动力360人,其中妇女120人(按国家规定50岁以上的女性不算劳动力),离县城约l5华里。村庄三面环山,土壤贫瘠,村庄男人主要靠到县城打工为生,年人均收入约2200元,属于贫困的山村。
一、H村就业市场现状
1、男性就业市场
H村男人大约1994年开始去县城打工,男人打工人数约占村庄男劳力总数的93%。男性就业除经营矿山、承包建筑工程外,大多集中在瓦工、钢筋工、暖气安装、自来水管道、装潢、木工等行业。
从经济收入的不同水平看,男性就业市场结构中呈现私营矿主、建筑业包工头、企业长期工和出卖劳动力的季节工四个层级。私营矿主:私营矿主仅有2户,其中一户是靠着1O多年与妻子开小卖部攒下的资本在县城开铸造厂,后来在矿山开采中致富,年收入约20万;另一户也是通过铁矿石倒买倒卖致富。建筑业包工头:包工头大约有10户,他们都是瓦工或木工出身,比一般的建筑工人有技术承包小型房屋建造工程,年收入约6万。企业长期工:长期工在国营或私营企业工作,收入虽少,但工资较稳定,年收入约14000元。季节工:以出卖简单劳动力(建筑工、钢筋工、木工)为生的季节工,处在男性性别分工的底层,他们的雇佣工资虽比长期工高,但冬闲4个月无事可干,年收入约8000元。
2、女性就业市场
女人外出打工的时问比男人大约晚10年。到现在为止,女人外出打工人数约占女劳力总数的20%。按照女性获得收入的多少及就业机会的差异,外出女工可分为房屋装潢女工、服装厂女工及打零工的妇女三个层级。装潢女工:H村装潢女工的工资与男人相差不大,年收入9000元,她们的收人成为家庭中重要的经济来源。村中有4位干装潢的妇女,都是利用娘家关系、朋友关系等进入早期的市场。服装厂女工:服装厂女工大多在恒泰服装厂上班(恒泰服装厂2005年兴建,从恒泰服装厂到H村有8华里,骑车需20分钟),据说恒泰服装厂刚开始招工时,有很多妇女报名参加,一直报了三天。但没过多久,很多妇女由于受不了恒泰服装厂严格的管理制度又都回来了。H村当时报名的大约有100多人,现在还在坚持干的只有l4人。服装厂女工每月收入500元,处于就业市场的下层。打零工的妇女:打零工的妇女处于女性就业市场的最底层,村庄男人偶尔会给这些妇女找一些零活,如,打草、建筑活计、砖厂临时工等,活计少,时间短,一年的收入仅1000元左右,对家庭生计的贡献微乎其微。上述三种情况表明,女性总体来看在就业市场中处于劣势,女性劳动收入的最上层只与男性就业的最低层——季节工在收入方面相类似。除了极少数女性因挤进男性的低层级就业领域而与男性就业市场形成交叉外,两个市场基本是分割和孤立的,女性就业整体处于边缘化和弱势化地位。
二、劳动就业的制度和政策
H村女性就业市场的形成既与村所在地政府的就业制度和政策有关,又与男权话语和女性的自我意识有关。
1、县级政府的就业政策
H村所属的县属于中等发展水平,县城北部出产铁矿和金矿,经济比较发达,县城南部以农地耕作为主,较为贫困。县劳动服务公司为促进劳动力转移就业实施了一些积极政策,但这些政策大多缺乏社会性别视角,主要表现为三点:
其一,职业的性别隔离严重。劳动法第l3条、妇女权益保障法第2l、22条都指明了用工时不得对妇女进行性别歧视,然而性别歧视的标准是什么,劳动法和妇女保障法并没有明确。妇女权益保障法在第23—26条列举了可能涉及的几方面歧视因素,却大多是从妇女的生理特点出发来维护妇女的就业权和健康权,由此造成我国就业歧视认定范围过于狭窄,现实中存在的大量就业性别歧视和性别隔离案例在法律上没有依据可循。H村所在的县城,男性干建筑、女性做服装几乎成为一种性别定型。另外,农村的男人大多集中在技术含量比较高的钳工、车工、电焊工等行业,女性集中在餐饮、商店等无多少技术含量的行业,政府对这种刻板的职业限定从未真正地加以审视和研究。县级就业政策没有给妇女冲破性别隔离提供制度保障,这是就业市场中性别分工的重要体制性因素。
其二,所有积极的就业政策中没有为妇女提供职业培训。劳动法第68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建立职业培训制度,按照国家规定提取和使用职业培训经费,根据本单位实际,有计划地对劳动者进行职业培训。从事技术工种的劳动者,上岗前必须经过培训。”这实际明确了在职业培训经费非常有限的情况下,只有从事技术工种的劳动者才有机会参加培训,而这种技术工人绝大多数以男性为主。在这种情况下,县劳动服务公司没有为在服装厂上班的妇女提供任何职业培训机会。
其三,缺乏男女同工同酬的详细规定。劳动法第46条指出,“工资分配应当遵循按劳分配原则,实行同工同酬”,而紧接着该法律第47条又指出,“用人单位根据本单位的生产经营特点和经济效益,依法自主确定本单位的工资分配方式和工资水平。”这实际容易使同工同酬的原则因单位的自由裁量度过大而失去效用。如,县建筑公司在一些建筑活计中,工地老板没有任何理由地克扣女工工资,并说是遵照惯例行事。由于劳动法、妇女权益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对于女性在职业准人、职业培训、工资收入等方面没有提供明晰的规定,导致基层政府和企业常常忽视法律。
2、工厂制度
恒泰服装厂工资之低和工时之长几乎达到了人的极限。服装厂女工敏说:“我做羽绒服,一天必须干100件活计,每件活计包括上拉链、熨商标、缝商标、里兜、外兜、画后片,一件活计只有0.157元一天必须干100件这样的活计,干13—14小时”服装厂女工的工资一般在月400元左右,而建筑小工的工资在月1200元左右,是女工的3倍。同样的用工制度,对工厂内不同身份的妇女也有区别对待。服装厂女工清说:“老板对家庭妇女和对小姑娘的态度都不一样,这庄里小姑娘好几天不上班再来了班长让照样干,也不扣工资。家庭妇女不上班,就说扣工资。扣工资家庭妇女还照样干。”可见工厂老板是利用妇女的家庭负担来压低已婚妇女的工资,工厂制与家庭、生育密不可分地结合在了一起。
3、村庄雇工政策
H村两委本身在涉及雇工等问题上也显示了自己的政策倾向。H村从1997年开始治理村庄道路,修桥垒护坝,道路硬化面积比以前大为增加,然而,村庄公共基础设施的建立和完善自始至终没有妇女参与,据副村长讲:“大队不让女的去,搞工程是重体力,搬砖、垒墙的。不太大的工程,村庄男劳力都有富裕。农村女的攀比厉害,让一个女的去,其他女的都要去,哪怕给1O元呢。女的在家里事也多,干不了多少活计。”谈话中体现了村庄雇工中男性优先的原则,即在男劳力还有充分剩余的情况下绝不可能让妇女参加体力劳动,这种原则的背后有牢固的支撑点,即“男外女内”的刻板分工模式及被社会定型的“妇女爱攀比”的性别文化观念在这种原则下,妇女完全被排除在村庄公共设施的劳动用工之外。
由此,劳动就业制度和政策中的性别规范、工厂制度的压制及村庄雇工中对妇女的排斥,这三者结合在一起,成为制约妇女就业的重要外部机制妇女就业处于极为困难的处境中,就业机会少,环境恶劣,且得不到各种支持。
三、家庭男权话语
性别意识不仅使劳动就业中的制度和政策在实践中以性别化的方式表现出来,而且也常以男权话语的形式在村庄中反复呈现。
1、阻止就业
H村的私营矿主和建筑业包工头约有12户,他们认为妇女的低薪工作对他们来讲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极力阻止妇女外出就业。26岁的伟是村里的私营矿主,他的年轻妻子没有工作,过着和城市人一样的生活。笔者问她,“想去打工吗?”她说,“丈夫不让去,说丢不起人。干啥去啊?一个月挣那么4(X)---500元钱?在家没意思,就给买了电脑,天天在网上聊天,还是没意思”。男人阻止了她就业的渴望,仅看到了工作的微薄收入,忽略了工作本身对妇女的意义,忽略了女性的自身经验和感受。
2、“非正式就业”是妇女的理想选择
阻止就业的情况在H村并不多见,更多的是主张“非正式就业”。做长期工或季节工的男人,认为妇女需承担农地耕作、儿童抚育及家务劳动的职责,因此与家庭相结合的农地耕作或小商品买卖,是妇女最理想的就业选择,妇女由此被严格地限制在家庭中。“零星”就业是另一种理想模式,妇女在农闲或其他男人允许的情况下从事一些零星的工作,赚取微薄收入,贴补家用。对此妇女自身怎么看呢?笔者访谈的88人中从事农耕和操持家务的妇女约有50多名,她们种植玉米一年纯利润约500元左右,相当于打工1O天的收入。妇女因此说,“破庄稼人没本事才种地,种地顶不了几个工”,表明了她们对农地耕作的否定和对外出打工的期望。
3、正式就业中的“补充”
妇女有时经过抗争也能争取到正式就业的机会和权利,但这种就业经常被认为是“补充”就业。村庄男人说:“县里属这村穷,要不怎么让女的去打工了呢?”“孩子生病后,妻子才打工的,就为了贴补点收入”。贴补家庭收入不仅是男人的一种意识,更从打工收入的差距中切实地反映出来。访谈的88名妇女中,16人外出打工(服装厂14人,装潢工2人),16人中个人收人超过家庭总收入45%的只有5位,其中3位是因为丈夫有工伤事故。约70%的妇女在外出就业中的收入远远低于丈夫的收入。
按照一般的标准,妇女收入占家庭收人的45%一55%被认为是经济独立,而收入在45%以下属于经济依赖,调查发现,绝大部分打工妇女的年收入只占家庭年总收入的20%一40%左右,在家庭经济中处于依赖地位。
四、女性的自我意识和表达
劳动就业的制度和政策、家庭男权话语成为制约妇女外出打工的重要外部因素,这些制度和话语在村庄日常生活中不断地被生产和再生产,渐渐内化为女性的意念,这种意念在某种程度上破坏了女性的主体意识。从访谈的情况来看,妇女对就业意义的认识和表达显示了一定的被动性和客体性。
首先,妇女就业意义的表达中没有凸显其个人意识。服装厂女工这样谈自己的工作:“上班主要是挣零花钱。干这一年,比种地强多了。”工资超过丈夫的木板厂工人琴说:“男人在工厂开钱不多,一个月才600多元,自己干好了一个月能有1000元。”但她又表示:“这么干就是帮助他,给孩子上学攒点学费,农村还是老爷们为主。”不管是服装厂的妇女,还是木板厂的女工,都把自己挣的钱看作零花钱,认为是帮助丈夫,贴补家用,这种意识其实是社会就业市场中的性别等级规则、家庭男权话语的一种内化。就业的性别分层中,女性就业收入中的最高层与男性就业收入中的低层相对应,社会就业市场对妇女是一个极大的排斥;家庭男权话语中,提倡女性的“非正式就业”,把妇女定位在家庭辅助的位置;这种状况使妇女不能积极看待自身劳动的意义,甚至贬低自己的劳动价值,把自己看作“挣零花钱的工人”。
其次,就业压力使妇女内心充满了矛盾和压抑。双重角色使妇女面临着极大的身心压力,H村的惠在服装厂干了一年,向笔者哭诉说:“工厂做工太累了。早晨6:00就得去,中午必须回来给孩子做饭,吃口饭就快走,恨不得吃不完就走,晚上再把活拿家来,干到夜里11、12点,一般人受不了这个苦。”惠的丈夫强烈反对惠做工,有一次竞把服装厂的活计塞到灶膛里烧了,惠有一段时间天天哭着干活计。H村的娟给别人刷涂料,她的丈夫抽烟、喝酒,夏天很少外出打工,娟有一年夏天去离家一百多里的三屯刷涂料,女的就她自己,回来后看到男人在家待着,心里特别不平衡。这种感觉实际是很多妇女在就业中面临的一种矛盾的抗争,是女性主体意识与男权意识的抗争:一方面妇女想冲破传统的“男外女内”的性别模式,在就业中寻求其自身的个体意义;另一方面,在与男权抗争的同时,还不能完全脱离原来的刻板模式,妇女自身又不断产生反抗争的意识,这种反抗争意识以各种抱怨性语言、对男人的责备等形式表现出来,如某妇女说:“要是男人能干,还用得着我这样吗?”表现了妇女对传统性别刻板模式的一种依恋。男权抗争与反抗争同时并存于一个统一体中,两者相互依存,共同发展。只有对男权的抗争完全取得了优势,性别作为支配社会现实的权力关系、作为决定各种制度规则的社会体制可能才会渐渐退出历史的舞台,给妇女真正的自由的自我。而当前,面对就业的沉重负担,妇女的反抗争意识不仅不会消失,而且在某些时候它可能还会随着对男权抗争意识的增强而增强,这样妇女在相当长一段时期仍无法摆脱出这种矛盾的桎梏,妇女的自我实现还需要漫长路程。
由上可见,H村就业市场中的性别现状,是社会性别机制及其背后的社会文化造成的,它既与宏观的就业制度和政策有关,又与家庭男权话语及将两者内化的妇女自我意识有关,是社会性别建构的结果。如果女性就业的制度政策和男权话语不可能在短时间变化,那么H村就业市场中的性别现状还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