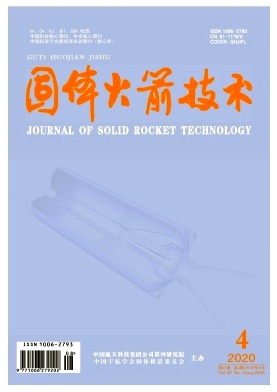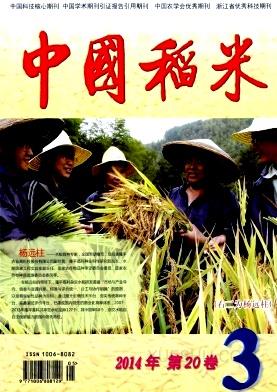关于现代文学中小资产阶级形象问题
现代中国新文学中,小资产阶级一直是一个“问题场”。将其纳入中国现代性研究的视野。可以考察中国文学中小资产阶级形象谱系的特征和嬗变。从一个独特的角度重新审视和反思新文学的内在演变。
现代中国文学中,小资产阶级(小资)一直是一个“问题场”。五四新文学以来,包括鲁迅、茅盾等许多重要作家的文学创作,以及“延安文学”直至20世纪80年代文学中涉及知识分子的作品,都与小资形象塑造和小资文化有紧密关系。鉴于现代中国文学中小资问题的突出性、复杂性和历史延续性。本文尝试做一个粗略的梳理,将其纳入中国现代性研究的视野,考察中国文学中小资形象谱系的特征和嬗变,从一个独特的角度重新审视和反思新文学的内在演变。
一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小资化
在西方,小资这个概念主要与马克思、列宁等人的论述有关,它们也基本决定了中国的政治家、文学家对于小资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身份、地位及其形象的认知。马克思的相关论述主要体现了小资产阶级在现代性上的落后性,注定成为历史悲喜剧中的不够光彩的角色。…列宁则在与形形色色社会主义思潮流派的斗争中,继承和发扬了马克思的话语,即指认对方代表小资产阶级立场来使之处于困扁的理论处境,小资产阶级已经不言自明地与幻想、空想、落后联系在一起。-2西方尤其是俄国有关小资产阶级的经典论述中,实际上建立了一整套涉及小资产阶级的理论范式、问题意识和话语模式。一种关于小资产阶级身份、形象的话语形态就这样被建构起来。
马克思和列宁等对小资产阶级的经典论述,决定了中国作家对本国小资产阶级的认识。但是,中国现代文学中,小资问题有自己的特殊性和着重之处,即现代知识分子的小资化的问题,以及整个现代文学的小资化问题。这意味着一种逐渐建构起来的知识社会学、文学社会学认知体系,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同构为小资产阶级,将中国现代文学的主体与小资产阶级文化对应起来。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既是代表着过去关于小资产阶级分析的总结,也确定了未来持续几十年的对于小资的评判态度和改造方式。在“讲话”中,小资产阶级问题基本上被处理为革命队伍中的知识分子问题,他们的立场、态度、意识、缺陷、身份,特别是与新兴的革命的现代民族国家政权的关系,以及他们与新的工农兵文艺的关系,都有了规定性的论述。
“讲话”中,小资产阶级主要指的是与城市、“新式教育”有关的中下层知识分子。从“讲话”开始。毛泽东对于现代中国的知识阶层的认知与他对于小资产阶级的叙述整合起来,小资产阶级问题彻底成为了知识分子问题,对于小资产阶级的批判和改造就是对于知识分子的批判和改造。
革命作为一种彻底的改造中国和全人类的现代性方案。它是衡量一切阶级、个人价值的终极标准。在“讲话”的“引言”中,毛泽东讲述了自己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而成长为革命者的故事。他通过讲述自己感情变化的经验,以现身说法的方式传达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改造的重要性和可行性——“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无独有偶,后来周恩来在《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1951年)中也象这样讲述自己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转化为革命者的故事。的确,鉴于众多革命领袖都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他们关于自己“感情变化的经验”的表白,既可以视为讲演中感染听众的修辞,也基本肯定了小资对于革命的态度和价值。这种关于小资的成长/改造的故事于是成为唯一一种经典的、合乎规范的关于小资的文学叙事。新的革命政权以其特有的革命现代性话语将小资的空间迁徙转化为时间(时代)跨越,“同志们很多是从上海亭子间来的。从亭子间到革命根据地,不但经历了两种地区,而且是经历了两个时代。到了革命根据地,就是到了中国历史几千年来空前未有的人民大众当权的时代。”
在一种典型现代意义的断裂性时间叙事结构中,给小资设定了一种迟到感、落后感,并与政治上的渺小和道德上的卑下相关,而这种叙事中小资的形象也被肮脏化:“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与工农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但精神有很多不干净处,就是身体也不干净,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大小资产阶级都干净。”’
自从“讲话”发表以来,在新政权、新国家的建立进程中,在革命意识形态的发展过程中,文学界的“批判小资产阶级”运动成为一个重要的手段,借助于此,一步一步强化了新的国家体系和新的文化秩序。这一针对知识分子的“小资产阶级批判”在毛泽东的“讲话”中完全确立起来,以后无论是在周恩来的《论知识分子的改造》,或是20世纪50、6o年代对于电影《关连长》、《我们夫妇之间》,小说<洼地上的战役》、《青春之歌》、《三家巷》的批判中,对于小资“立场”、“意识”、“情调”的规训和批判越来越激烈。知识分子的小资化,“小资产阶级情调”成为文学创作、文化批判、政治批判中人们能够熟练运用的概念和话语策略,也为自认为小资的知识分子们自我批判、反省时习惯性地运用。小资实际上已经成为许多知识分子自我认同并矮化自己的概念。
二 文学中的小资形象谱系
尽管小资虽然似乎有自己的阶级实体,他们主要仍是一个文学想像和塑型的问题,是各个时代的无数文本中逐渐塑造出来的一种复杂形象,是一些叙事和描述的产物.因为他们合乎某些特定的质素,而被认为(自认为)是小资,具有了小资产阶级性。
中国现代文学的“新人”想像的文本呈现,其中现代性的具体趋向及其各种现代焦灼,都与小资这一问题场密切相关。小资,就现代意味而言,正是现代中国“新人”的主要部分,他们参与了中国现代史每一次重大进程。小资由“新人”转为“旧人”,由“现代人”转为“落伍者”,由“先锋队”转为“被改造的对象”,翻云覆雨,腾挪翻转。通过探讨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文学所制造的小资形象谱系,可以藉以了解中国现代主体形象的形塑和嬗变。
例如,“五四”文学的核心就是如何去想像、塑造“新青年”形象。如郁达夫《沉沦》中的“他”,鲁迅《伤逝》中的涓生、子君,庐隐《海滨故人》中早期的知识女性,叶圣陶笔下的倪焕之等,都是些小资,他们是近现代文化生产/传播机构的产物,学习了西洋传人的近现代知识,接受了诸如“个性解放”、“个人主义”、“自由”、“民主”、“自由恋爱”、“婚姻自主”等等观念,熟悉西方近现代的文学、文化符号。从而成为一群现代“观念人”。他们经由学校中的新锐老师以及新刊物、新文学接受了新的词汇,沉浸于一种非传统的观念世界和情感世界。
第二阶段,接受了“五四”新青年的别样的人生的冲击后,新成长起来的“新人”,成为文学中的流浪小资形象。茅盾的《蚀》、《路》,巴金的《灭亡》、《新生》,丁玲的《梦珂》、《莎菲女士日记》,等等,塑造了一些失业的大学生、无政府主义者、浪漫的革命家形象,他们从传统文化人伦规范和生活方式中逃逸出来,进入上海、北京这样光怪陆离的都市。他们大都未能被编织到现代都市社会结构,而在都市的底层和边缘当“高等游民”。由于进入全球化的文化生产/传播体系的中国“孤岛”,他们获得强烈的现代意识,但与半殖民地本土中国相互隔阂、疏离。他们或是在情欲中煎熬或放纵,或是陷入颓废主义的深渊,或怀着无政府主义悲天悯人的道德义愤。都市流浪小资形象是中国较早有都市感震惊感的形象,暗含着新的现代主义美学。
小资革命者形象是20世纪3O年代上海滩的革命海派文学中所塑造的小知识分子出身的“新兴阶级”革命者,他们由都会中流浪的小资形象直接转化而来。当时,马克思主义、列宁的建党学说、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弥赛亚情结共同形成一种布尔什维克式的革命现代性,并在中国传播开来。小资革命者文学形象,意味着一部分知识分子借助革命来解决自己的身份归属焦虑,他们在革命上体现出激烈的“先锋性”和“狂热性”,满足了自己的历史主体感和民粹主义情感。但是暴力革命要求的集体主义、牺牲精神、钢铁意志等,又不是每个小资都具备的,于是,这些早期的布尔什维克主义革命者形象中,进裂出来种种分裂性的人格和情绪。例如,在“革命加恋爱”小说中出现了既有布尔什维克气质,又挣扎于世纪末式的颓废气息的小资革命者,在革命罗曼蒂克文学中,逐渐展现了朝气蓬勃、伟岸强健、坚强彪悍的“无产英雄”,但其实还是小资的革命狂想。
从丁玲的《在医院中》,到宗璞的《红豆》,到杨沫的《青春之歌》、欧阳山的《三家巷》、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构成了一个小资“新人”的成长故事,这些小资“新人”与其说是一群反叛者,不如说是一群精神皈依者、个性的被规训者和身份的被组织者。在新的政权起源、发展的宏大叙事中,小资“新人”由天真幼稚的自发反抗者经历种种考验、磨难,艰难地成长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这种成长归因于神圣的归属感,先行者圣洁崇高的道德感召,更归因于组织和纪律,领袖的神圣教谕。但是,“延安文学”以来工农兵文艺的新人谱系中,工农兵形象才是中心,小资处于边缘化。
三 小资情调的文化空间
小资文化空间,一方面意味着小资是现代文化资本的拥有者,他们通过新式教育和文化机构,获得了新的知识和新的观念;另一方面又必定呈现出其它多种文化力量对它的影响,甚至决定了它能否存在或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存在。几乎绝大多数中国现代作家都与“小资情调”有某种关系,这既是指对他们社会身份的阶级划分,也是指他们的表意系统(包括其作品和生活方式)中流露的“趣味”、“情调”。“小资情调”其实是一个变动又相对独立的文化区隔,涉及一整套符码操作、知识资源和情感表征,它构成一个意象化的小资精神空间。
例如,在郁达夫的《沉沦》中,作者非常细致地、反复地描述异域校园生活的“他”阅读西文原著的姿态,意味着小资新青年的“新”其实是一种“知识”上的新,他们较早获得了来自西方的近现代文化符号,主要的途径是通过文学。新文学中,大量出现西方原文语汇或音译语汇(如普罗文学鼓吹者笔下的“意德沃洛维基”之类),不能简单地被视为一种不成熟的语言写作形态,而应该重视其符号表意功能和叙事功能。文本中,大量显示叙述者及其笔下人物掌握的新文化资本,给予了叙述者某种知识上的优越感,这牵涉到新的教育背景和新的认知体系,派生出某种“现代”情绪和观念。
小资所掌握的文化资本,许多是文学化的情绪、意象和叙事,核心是一些新观念和新情感。这些现代观念在西方起源时的政治、经济、人文的历史土壤,与当时的中国迥异,于是它们在中国只是一个漂浮的浅层。但是,这些镶嵌着新文化符号的文学作品,逐步借助都市新文化的出版、发行系统,和使之经典化的圈内人评议,传播至那些正在或已经接受了程度不一的现代教育的读者。这些沉醉的接受者,莫不在想像中形成了自己对于周边世界、对于“旧文学”、对于“旧文化”的权力关系,扑面而来的西方文化符号向他们呈现一个新的文化空间,对世界秩序的认知在重新组织和养成。一个独特的现代中国的小资文化空间开始建构。
到了2O世纪3O年代左右,在茅盾等人的小说中,小资文化空间扩张了。茅盾的小说刻意营造了一个都会世界的新社群——以小资“时代女性”为中心的圈子。小资青年男女“圈子”的聚会、交谈等各种类似于沙龙的活动组成茅盾小资叙事的重要成份。《追求》中,章秋柳等人离开大学后,依然主要生活在由同学会构成的圈子中。“圈子”有多种功能,它是小资们的社会资本,又是一个共享的话语场和情感空间。“五四”时代的小说染上了强烈的“倾诉”瘾,其文本许多是采用独自体的“自叙传”,以一个孤冷的小资青年面对读者喷吐伤感而滥情的话语来表现。而茅盾的小说中,小资们的“对话”(包括书信往来)成为文本中非常重要的景观,他们依然有强烈的“倾诉”瘾,但这种表达的欲望通过共享各种话语场获得释放。茅盾小说中的小资青年男女共享一种说话的方式,共享一整套知识体系和文化符号体系,共同领略各种只有他们之间才能如此畅所欲言的长篇大论,共同沉浸入一种只有他们才能欣然领会的表情、神态和情境中。这些实际上提供了一种小资的集体认同,以及小资的公共空间。
小资文化空间依存于晚清以来并在五四时期开始突进的现代教育体系和大众传播产业。从留学生制度到大都市的高等学府到散布于全国城乡的师范学校、中学和小学,从《新青年》、《小说月报》、《现代》这样的“高雅”的思想、文学刊物,到被它们影响、刺激下产生的各种聚聚散散的社团推出的五花八门的次一级刊物、杂志乃至学生社团创办的各种非正式的油印刊物、小报、壁报,再到各种报纸推出的副刊以及报纸主体报道、社论,都在向受众传递种种驳杂的观念、知识、故事、意象和情调,小资文化空间也就逐渐清晰。同被指认为阶级实体的小资一样,小资文化空间也经历了起起落落的波折,从延安整风运动开始,小资文化及“小资情调”总是遭到规训和整肃,但是一到文艺政策稍微宽松,又总是顽固地显露,如丁玲延安时期的小说、杨沫的《青春之歌》、欧阳山的《三家巷》等,以及《早春二月》等电影,等等。
有意思的是,到了2O世纪9O年代以后的上海等都市,“小资写作”和“小资情调”又再次充分生产和膨胀。看来,无论在2O世纪哪个历史阶段,小资们都在他们的文化生产、流通场所,运用他们的文化资本,创造、传播着带有小资情调的文本,与各种其它的文化样式冲突、纠缠着,延续着小资文化空间,从而构成理解现代文学的一条别有意味的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