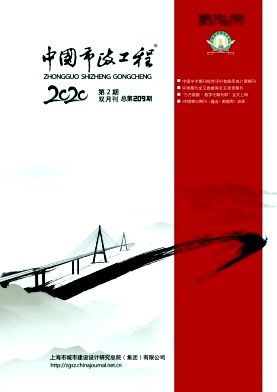清音余韵话民俗——京派乡土小说民俗风情的文化价值与审美特性
京派小说家以大量的篇幅描绘了乡村生活特有的风俗画,表现出浓郁的民俗色彩和素朴的民俗美。文学作品对独特的民俗色彩的展示,不仅是一种生活现象的展示,而且也是一种生活本质的揭示。对民俗文化的研究有助于深入到历史中,透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揭示其独特的文化价值与审美特性。
我国是个多民族国家,不同的地域有着不同的民俗,俗话说:“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沈从文的故乡湘西凤凰,废名的故乡湖北黄梅.汪曾祺的故乡江南水乡高邮,故乡的地域文化环境给了他们以柔美、清丽、隽逸的地域文化熏陶淳厚素朴的风土人情、婚丧嫁娶的习俗禁忌、饮食起居、歌谣谚语、节日娱乐等独特的民俗文化对京派作家产生了潜在影响。京派小说家以大量的篇幅描绘了乡村生活特有的风俗画,其作品呈现出景物的美、意境的美、神韵的美,表现出浓郁的民俗色彩和素朴的民俗之美。沈从文的作品之所以能飞跃国界,为世界人民所喜爱,正是由于它具有相当浓郁的地方和民族特色。沈从文的湘西系列小说正是以x/,湘西苗汉各族特有的婚姻、节日等习俗的传神描绘,构成了他小说独有的情调,奠定了他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正是因为这些民俗特色,大大增加了他的说的艺术魅力。沈从文在他的作品里给我们展示了一幅由湘西汉、苗、土家各族文化交织成的复杂而又多彩的民俗生活画卷。打开沈从文的作品,湘西美丽的山山水水和奇特的风俗人情便纷至沓来:碧水环绕的山城,元霄的爆竹烟火,如雷的鼓声,端午的龙舟竞赛,中秋的舞龙耍狮,月夜的对歌,点着火把走夜路,军民同乐,孩子的取名。迎婚送亲的唢呐声.办丧事的绕棺下葬等等,无不新奇别致。这些山花流水般绚丽神奇的风俗画面.散发着泥土的清香,显示了湘西山城浓郁的民族特色和地方情调,使人神往.令人陶醉。给《边城》增添了一份独特的魅力。
时令节民俗,是一种极其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它一般是指一年之中随季节、时序的变化,在人们生活中形成的不同的民俗事象和传承。在时序、季节的变化之中,各民族都有自己传统的节El,在这些节日中,最易显示出各民族的民俗特征。沈从文在《边城》中这样写道:“端午日,当地妇女、小孩子,莫不穿了新衣,额角上用雄黄蘸酒画个王字。大约上午十一点左右,全茶峒人就吃了午饭,莫不倒锁了门,全家到河边看赛船。”为了增加这节日的气氛,人们还“把三十只绿头长颈雄鸭颈脖上缚了红布条子,放入河中,让人自由下水追赶鸭子。不拘谁把鸭子捉到,谁就成为这鸭子的主人。船和船的竞赛,人和鸭子的竞赛,直到天晚方能完事”。Il1这样的喜庆风俗是何等优美啊!由于沈从文的湘西风俗描写深刻地揭示了湘西人民,特别是苗族人民的民族文化心理,我们读着他的作品,不但随笔入境,而且止不住掩卷沉思,发现这神秘的背后,隐藏了动人的悲剧,同时也隐藏了动人的诗。优美中含有粗野,柔美中含有忧愁,正是这优美、古朴、奇异的风俗和令人伤心的美,深深地感染了读者。端午节中的划龙船,这是一种湘西特有的文化。这种文化不受外来文化的影响,保存的是自己民族固有的风俗习惯。而这些风俗又渐渐演变成了一种传统.划龙船的民俗积淀着深厚的民族传统和民族文化内涵,这种民俗一旦进入了文本就打上了作者强烈的主观感情色彩。沈从文的代表作《边城》四次写到了龙船比赛,仔细审视详略不同的四次划龙船,都会有不同的发现。作者较为细腻地描绘了湘西端午节赛龙舟中人们的装束、打扮到龙舟的形状,及其龙舟竞发的场面都被刻划得细致人微。那两头高高翘起,船身绘着朱红色的龙舟。头上和腰间缠着红布的青年浆手,那起劲的鼓声,离弦而发的长龙,还有两岸无数“观战”的人的呐喊助威,那红火得近似疯狂的抢鸭子的场面.甚至还没有尽兴的赛手们在月光下玩上个半夜,妇女、小孩子们额角上用雄黄醮酒写“王”字;赛龙船敲的高脚鼓“用牛皮蒙好,绘有朱红太极图”。深夜中老道拿着纸幡引路,孝子第二,杨马兵殿后,绕着寂寞棺木慢慢转着圈子。旁边有人打着锣钹.老道闭着眼且走且唱.用杂色纸花,撒向棺木,象征亡灵升上极乐世界的丧葬仪式。这一切痴狂的场面.古老而健康的风俗.正反映了湘西人民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幸福的追求。湘西沅水一带特有的地方风情,湘西人民的粗犷放达的性格和心理。都在这龙舟竞渡的民俗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宣泄。
《边城》里茶峒渡口的老船夫,免费招待烟茶,拒绝过客报答,总是待人以诚,存心与人为善;像《长河》里写当地人“赶场”进行交易时,成交以前必盟神发誓.成交后还得在附近吃食摊子上去喝酒挂红,“若发生了纠纷.上庙去盟神明心时,还必须用~只雄鸡,在神座前咬鸡头各吃一杯血酒,神方能作见证”。从这种传统的原始民风里,让我们看到了当地劳动人民的浑厚、正直和朴素。写湘西女子有爱美的天性,但她们审美的标志如头发挽成一个大髻.缠上一匹一丈六尺的绉绸手帕,以及那打扮在身上的精心编织的、百种千般各具其妙的纹样和色彩的“苗带”,表现出一种特有的风情美。写湘西房屋建筑的奇特.如傍山作屋舍.临水建吊脚楼,村中多庙宇祠堂,这都与当地的地理条件和人们其俗信鬼而好祠等多种信仰分不开。作者从富有民族特色从而使他的湘西小说具有了丰厚的审美内涵。沈从文这些描写湘西风俗画的作品。使他获得了“湘西边区少数民族生活的画家”的赞誉。
汪曾祺常常称自己的小说为风俗画小说。他认为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生活的抒情诗,它保留着一个民族的童心,它使一个民族永不衰老。这样,抽象的、看不见摸不着的民族感情就浸润在风俗之中。所以,汪曾祺的风俗画不仅为人物营构了氛围,而且更反映出了特定环境中永不衰老的民族精神。它蕴涵着汪曾祺的美学认识:美的事物,美的情操,必须交融在美的艺术境界里,才能突显出来。他的小说与民俗确实有着非常广泛的联系。汪曾祺叙写自己从小所体验过的生活,内容广泛,涉及到风俗的很多方面,诸如礼仪、岁时、娱乐等,他的作品往往从而成为一幅幅饶有兴味的风俗画。如他的小说《陈四》,全篇4000多字抒写了迎神赛会的风俗民情,酝化出一种原始的、古朴的“欢乐”情调,酿造出一股朴野粗犷的文化氛围。后文仅用几百字点出了踩高跷的陈四就在这种蒙昧的氛围中挨打、大病、卖灯等等,人物被浸泡在浓重的古~I-N,习之中。如迎会的场面:那真是万人空巷。倾城出观。到那天,凡城隍所经的耍闹之处的店铺就做好了准备:燃香烛,挂宫灯,在店堂前面和临街的柜台里面放好了长凳,有楼的则把楼窗全部打开.烧好了茶水.等着东家和熟主顾人家的眷属光I临。这时正是各种瓜果下来的时候,牛角酥、奶奶哼f一种很“面”的香瓜1、红瓤西瓜、三白西瓜、鸭梨、槟子、海棠、石榴,都已上市,瓜香果味,飘满一街。各种卖吃食的都来了。老太太、大小姐、小少爷、老太太手里拿着檀香佛珠。大小姐衣襟上挂着一串白兰花。佣人手里提着食盒,里面是兴化饼子、糕,各种精细点心。远远听见鞭炮声、锣鼓声,“来了,来了!”于是各自坐好,等着。接着讲述了自己家乡的赛会与鲁迅先生所描写的绍兴赛会的不同,将赛城隍的各个方面写得淋漓尽致。
汪曾祺的笔下,并没有自然主义地表现风物本身,而是以风物为作品的细节,透过它与民情风俗相联系的现象。表现生活的广度.加深作品的历史深度,从而扩大了作品的容量。风土情,不仅仅是一种现实的存在,也是千百年来民族历史的产物,民族文化的缩影。小说、散文中浓郁的地域文化色彩,正是民族特色的表现。再如《大淖记事》,文章一开篇就极力描绘大淖四时景物和风土人情.这里人的生活、风格、是非标准、伦理道德观念与街里穿长衣念过“子日”的人完全不同,特别是他们的婚俗,大淖开化得很,“这里人家的婚嫁极少明媒正娶”,“媳妇多是自己跑来的姑娘一般是自己找人。在这样一种风俗的制约下,倘若巧云安分守己,巧云与十一子明媒正娶反而显得“离经叛道”了。入乡随俗.巧云妈的私奔和巧云与十一子的相好。正是在这种环境里.才显得自然生动,富有大淖气息。
在京派小说的文学视界里。农村和农民是中国古老风俗的创制者和传承者,乡风民俗具有无比丰富的历史内容和生命内涵,它们沉潜于民族历史的皱褶之中,弥散在乡村民众的气息之间。这种民间文化形态以持久坚韧而又诗意盎然的方式,规范支配着乡土中人自然淳朴的生命气质和人生形式,也成为他们行为的心理渊源和价值向导。正是在这样审美观照之下。废名的乡土小说在20世纪中国乡村文学的叙事中,散发出与众不同的独特魅力。废名小说以美伦美奂的风俗描写展开对乡土家园的审美发现,其作品不论是以情取胜的《桥》,还是以理取胜的《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都以大量篇幅将乡土风情如艺术画卷般次第展开。在这一幅幅的艺术画卷中,风俗描写不是底色,也不是背景,而是承载其作品意义的骨架和血肉,《桥》中没有一个性格鲜明的人物,而即使没有小林、琴子这些角色,《桥》中的风物礼俗依然如画如诗。《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大量的风俗片段更可篇篇独立,皆成美文。废名站在20世纪启蒙话语对民俗文化彻底批判的对面,视乡风民俗为中国民问社会的集体抒情,从《桥》中尽言其美,到《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发现其用,以独特的审美视角尽显乡风民俗之社会功能,从而使有世外桃源美誉的废名小说于审美价值之外更具有了独特的社会学价值。
民俗是同人们生活发生着最密切关系的文化事象.人们生活在民俗里,好像鱼儿生活在水里。的确,乡风民俗与乡村大地是水乳交融的。风俗是文化沉积的标记,人类以此追寻自己的文化根脉。对乡村中国民间风俗的复杂内涵及其社会功能的深入挖掘,不仅显示出乡村民间文化形态对于乡村人物精神世界多方面、多层次的制约与塑造,更将民间文化之于乡村中国的意义价值全面呈现出来,京派小说的民俗文化观也因此而具有了独特的审美价值和社会学意义。民俗文化的研究不但要放到中华民族文化系统中去考量.还要在文学系统中考察意象的发展及给文学带来的影响,研究审美意象在文学史中的变化、影响。作家在作品中表现着特定地区的民俗事象和民俗生活风尚,一方面通过对地方文化色彩的描绘.显示出一种鲜明的地方特色:另一方面这种特定地域的民俗事象的描绘一旦融入社会历史与民族心理的特定内涵.就暗示和体现出更加深广和普遍的社会意义。这种地方特色不仅存在于不同作家群体关于不同地域民俗事象的集体表现之中,而且也深刻的灌注成作家特有的个性和风格。可见由此表现的地域文化特色不同,作家的创作个性及风格也各不相同。文学作品对独特的民俗事象的展示.不仅是一种生活现象的展示,而且也是一种生活本质的揭示.这正是不同的文学大师笔下的生活显示出清晰的不同分野的原因。正因为如此我们看见北京风味的胡同院落、茶馆、店铺和那具有幽默感的京味语言,就会判定是老舍的作品;而看见具有浓郁湘西边地风情的吊脚楼、划龙船、端午节、奉神信巫等就会想到是出自于沈从文的手笔。
一个民族特有的风士人情、道德价值观、宗教信仰、节庆仪式、人生礼仪、生活习俗等,是一个民族历史文化传统和心理素质的具体体现,是“一个国家和民族中广大人民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文学作品的生命力,往往取决于作品民族化的程度,而文学作品是否有民族独特性则和它所展示的民俗化内容密切相关。民俗化倾向的文艺作品,只有从具体的民俗描写中.展示民族独特的风俗人情,才能构成其内容和形式的民族化特色。可见民族特色常常是由风俗习惯作为标志体系,京派作家一贯坚持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上去观察人、研究人和表现人,所以,他们笔下的民俗没有停留在纯粹民俗事象的描写上,而是包藏和浸润着深厚的文化意蕴。
京派作家在小说中努力展现城乡人情世态、民风、民俗的良苦用心,显示了作家们相当自觉、相当浓厚的文化批评意识。就是这种文化意识,促使作家以一种宏观的文化目光来历史的、客观的审视中华民族的过去与现状,抨击“丑”的弘扬“美”的传统文化以促进民族的自尊、自立与自强。风俗体现了一个民族对生活挚爱乐观和从生活中感受到的愉悦,体现了一个民族丰富多采的生活方式和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民俗自身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价值和审美意蕴。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风俗民情作为一种现实的存在,已经成为千百年来民族历史的产物和民族文化的缩影。它既是实实在在的物象,又是民族意识和民族心理的载体。它既是某一地域特色生活的表现,同时也反映了整个民族共同具有的特征。沈从文描写了神巫跳摊的仪式(《神巫之爱》)和男女对歌的恋爱方式(《龙朱》等)。废名描绘了农民进城烧香的规矩(《文公庙》)。萧乾《俘虏》中的七月节和废名《桥》中清明节的描绘都鲜明生动、兴趣盎然。《边城》对湘西端午节的描绘更为成功。不同于“五四”时期那些揭示故乡人民生活悲剧和精神状态的乡土小说(如许杰的《惨雾》、赛先艾的《水葬》、台静农的《红灯》等),京派作家偏重于对民族风情的静态审美观照,他们无意于深入剖析农村社会的现实境况,他们的兴趣在于表现生活的特定的美的内涵。出现在京派小说中的风景是美丽的田园风光,风俗则主要是那些表现了民族特色而又不违反自然、健康原则的乡风民俗。京派小说家这种向乡村自然生活皈依的态度,反映了他们与自然和谐一致、执守中道的传统精神和以中正平和的眼光对待民族文化基质的审美态度。
通过京派小说诸多的民俗事象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民俗与文学的血缘关系是客观存在的。民俗和文学究其产生,常常是二者合一,相生相伴,互融渗透,密不可分。没有民俗就没有文学,没有文学,民俗也就无法传承和保存。京派作家巧妙地运用民俗的特殊功能,把它创造性地转化为艺术细胞,尽管小说中的民俗描写并非是处处“匠心独运”,有不少地方是随文而出,随笔点染,但都成为了小说有机体上不可能少的血肉。文学作品要表现社会生活.也要表现社会情绪,离不开富有民族色彩的风土人情、世态习俗。故此,民俗也成为作家文学创作的源泉,对民俗文化的研究有助于深入到历史中.透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揭示其独特的审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