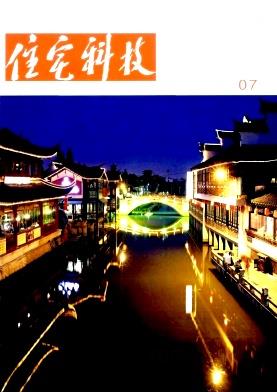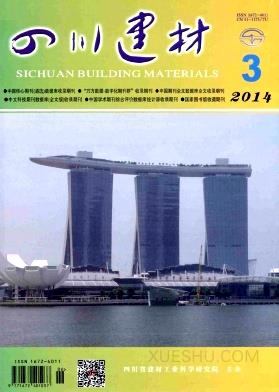浅谈边塞诗在晚唐的余韵与沉响
边塞诗作为唐诗中的一株奇葩,历来备受人们青睐。它在唐代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经历了萌芽、产生、发展、繁荣、衰落乃至日渐沉寂的过程。人们对边塞诗的关注,往往着眼于初唐、盛唐和中唐时期,留连于盛唐明朗壮大的气势和中唐哀怨幽婉的意蕴,而对边塞诗在晚唐的回响、余韵乃至沉寂的原因却大多忽略或漠视。其实,晚唐边塞诗在衰落和消亡的过程中,也留下了它自己的特点。
边塞诗是唐诗的重要一脉。人们论及边塞诗,主要聚焦于昂扬壮大、雄奇豪迈的以岑参、高适、王昌龄为代表的盛唐歌行体或七言绝句,后虽逐渐将视点转至深邃古拙、哀婉悲怨的以李益、卢纶等为代表的中唐以五古、五律为主要形式的边塞诗。但似乎边塞诗到此便戛然而止。其实,作为一种唐代极具特色与代表性的文学现象和诗歌题材。自有它滥觞、发展和沉响的全过程,它不可能横空出世后无故就销声匿迹。仔细考察整个唐代边塞诗,我们不难发现,虽然晚唐边塞诗随着文运、世运而日渐衰落,但的确也还存在一个相当长的延续过程。且因时代环境、诗人心态的变化而表现出与盛唐、中唐边塞诗迥然不同的特点。
一
由于晚唐国势日渐衰微,各种社会危机日趋严重,宦官专权、藩镇割据、朋党之争、边患频仍,统治者忙于自救,已完全失去了盛唐、中唐时期开疆拓土、成就帝王大业的气魄。文人士子也因时运艰难,失去了往日立功边塞、从军幕府的豪情,边塞诗的创作主体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既没有了像岑参、高适那种长期投身军幕、对边塞充满神奇向往并热情讴歌边塞生活的大诗人,也没有中唐像李益那样几度出塞、对边塞战争有深切体会、倾心创作边塞诗的名家。晚唐边塞诗非常分散。几乎整个晚唐诗中都有边塞诗的影子,却又缺少集中创作边塞诗的一流大家和遗响千古的名篇。然而。在一些中小作家的诗中,还是存在着一定数量、且有一定质量的边塞诗。如果以长庆四年作为中、晚唐分界的话,晚唐则在姚合、张诂、薛逢、项斯、马戴、李频、曹邺、高骈、雍陶、许棠、曹松等人的诗中,时有边塞佳篇闪现。而比较集中、有一定特色的往往是那些或为边将、或有较长的军幕生涯、或有一定游边经历的诗人创作的,如马戴、张枯、高骈、曹松、雍陶、李山甫等。由于他们的边塞诗是产生在对边塞生活的亲身体验的基础之上。所以能对晚唐边塞生活作较为全面的直接观照,又能结合晚唐病态社会的时代气息,注入自己的切身感受,抒写出既和盛唐、中唐边塞诗一脉相连。又深深打上晚唐烙印的大漠之声。
晚唐边塞诗和盛、中唐边塞诗之差别,首先表现在诗歌主题格调的改变上。由于盛唐边塞诗是产生于王朝鼎盛、国势煊赫的氛围中。尚武轻文、开疆拓士成为统治者的基本方略,从军边塞、建功立业是文人士子追求自我价值的最佳构想,因此,此期的边塞诗的主题主要是讴歌战争、粉饰沙场、弘扬牺牲精神的,其格调显得昂扬向上,慷慨悲壮。“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书生”,“愿将腰下剑,直教斩楼兰”,“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在诗歌中始终激荡着驰骋疆场、马革裹尸的英雄豪气。即使偶尔有“死是征人死,功是将军功”,“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的不平与哀思,但决非初、盛唐时期边塞诗的主旋律。中唐边塞诗已没有盛唐时期的那种磅礴大气。频繁的边患和此起彼伏的内乱,使唐帝国始终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社会矛盾和文人心态日趋多元化。统治者失去了往日开边拓土的能力与气魄,总是在顾此失彼中张皇失措。虽然安史之乱后也曾频繁地调兵遣将,但其主要的心力已经转向内部改革和平定内乱。如大历、贞元年间的改革漕运和税法,永贞、元和年间政治革新和军事削藩等,这自然会引起中唐诗坛整体格局的变化。其主格调由盛唐的豪放之歌变成了边塞之怨,“由言志述怀的宗旨换成了感事写意”,“边塞题材在唐人创作中一变而为对社会忧郁”。但由于盛唐气象在中唐还存有余绪,贞元、元和间的脆弱“中兴”又给文人士子们太多的虚幻理想,因此,中唐的边塞诗在以“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碛里征人三十万,一时回首月中看”的厌战、怨战声中,仍有鼓吹杀敌报国的。如“将军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男儿当为国,破敌如摧山”的靼鞑铿锵之声,还多少带有些盛唐边塞诗之遗响。然而,晚唐却由于时局的江河日下,不可挽回,创作主体的心态已堕入消沉与绝望的深渊,边塞诗也就一变而为反战、休战的呼声而显得异常的凄厉与沉痛。考察晚唐边塞诗主题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一是极力描绘边塞战争的血腥肃杀之气,以抨击朝廷的平戎失策给士卒带来的沉重灾难。如李山甫《兵后寻边三首》之一:“风怒边沙进铁衣,胡儿胡马正骄肥。将军对阵谁教人,战士辞营不道归。新血溅红粘蔓草,旧骸堆白映寒晖。胸中自有销兵术,欲向何门说是非。”之三:“旗头指处见黄埃,万马横驰鹘翅回。剑戟远腥凝血在,山河先暗阵云来。角声恶杀悲与哭,鼓势争强怒若雷。日暮却登寒垒望,饱鸱清啸伏尸堆”。如此直接地描绘边塞战场的血腥与恐怖,是任何盛、中唐边塞诗所未曾有过的。从诗中我们可以间接读出诗人对战争的强烈反感和对生命的深沉呼唤。“战士辞营不道归”再也不是“欲饮琵琶马上催”那样的浪漫与洒脱,而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和苍凉。
如果说盛唐边卒从容就死有明确的价值指归的话,那么晚唐士卒的无奈殉难就带有明显的湖涂性。晚唐边塞诗对生死的价值做了比盛、中唐更加理性的思考:既精到的描绘残酷的现实,还深沉的追索战争的负面意义和造成悲剧的根源一统治者对士卒生命的贱视和安边御侮的失策。第二种方式是用抒怀、寄远、怀远的方式直接抒发对战争的憎恨与反感。如马戴《塞下曲》:“旌旗倒北风,霜霰逐南鸿。夜救龙城急,朝焚虏帐空。骨销金镞在,鬓改玉关中。却想羲轩氏,无人尚战功”。曹松的《己亥岁二首》:“泽国江山入战图,生民何计乐樵苏。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传闻一战百神愁,两岸疆兵过未休。谁道沧江总无事,近来长共血争流”。高骈《塞上寄家兄》:“栎萼分张信使稀,几多乡泪湿征衣。笳声未断肠先断,万里胡天鸟不飞”。由于马戴在会昌末至大中年间的一个较长时期在太原军幕,其边塞诗主要作于此时,因有切肤感受,故其边塞诗写得格外真切、悲怆,反战的呼声也就更为急切、直接。高骈是晚唐朝廷倚重的边将,但在他的诗中却明显地感到消沉和悲凉气氛,极少有纵横沙场、引兵杀敌的斗志和豪情。就是在他受诏领军时的《言怀诗》里,也是“恨乏平戎策,惭登拜将坛。手持金钺冷,身挂铁衣寒。主圣扶持易,深恩报效难。三边尤未尽,何敢便休官”的“易水悲歌”似的感慨,给人以知其不可为而勉强为之的独木难支之感。他的边塞诗如《边城听角》、《塞上曲》二首、《边方春兴》等均是低回绝望的格调,几乎找不到半点阳刚健朗之气。作为边关将帅之诗如此,边塞诗在晚唐的格调自然可窥一斑。和他相比,曹松的边塞诗的反战意味显得更激越和直接一些:“谁道沧江总无事,近来长共血争流”,“请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近乎对边塞战争赤裸裸的揭露和对战争意义的彻底否定。三是通过游边的文人士子对战后疆场荒败景象的客观描绘,揭示战争给人类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如李咸用《垅头行》:“行人何彷徨,垅头水呜咽。寒沙战鬼愁,白骨风霜切。薄日朦胧秋,怨气阴云结。杀成边将名,名著生灵灭。”李山甫的《兵后寻边三首》之三;“千里烟沙尽日昏,战余烧罢闭重门。新成剑戟皆农器。旧着衣裳尽血痕。卷地朔风吹白骨,拄天青气泣幽魂。白怜长策无人问,羞戴儒冠傍塞垣”。从这些诗歌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如同汉末“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阴森可怖的气氛。“杀成边将名,名著生灵灭”,将边将和百姓进行直观对比,冷静地剖析战争的意义。“新成剑戟皆农器,旧着衣裳尽血痕”是对战争破坏人们正常生活,迫使他们趋身锋镝、血染疆场的直接揭露和抨击,痛心疾首里透露出对和平的向往与期待。还有许多游边诗体现了这一共同特点,如于渍的《塞下曲》、姚鹄的《边游》、雍陶的《罢还边将》、丁棱的《塞下曲》等。四是晚唐还存在一些反映西南边陲和“南蛮”之间战事的边塞诗。从八世纪中叶开始,“南蛮”不断入寇,尤其在宣宗大中年间和懿宗咸通年间,唐与南诏之间的关系近乎破裂,战事连绵,西南川、滇、桂乃至湘、黔地带屡屡有“蛮民”的入侵或反叛,西南地区成为新的边塞。如《资治通鉴》载:“咸通二年春,懿宗诏发邕管及邻道兵,救南安,击南蛮”“四年三月,南蛮寇左右江,侵逼邕州”“五年…南诏帅群蛮近六万寇邕州…甫毕,蛮军合围”。对于这段时期蛮汉战争之惨烈的记载,在晚唐樊绰的<蛮书>中有更加详细的描述:“咸通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蛮贼逼交州城,河蛮在苏历旧城置营,及分布贼众在排筏士仅二千余人……”“咸通四年正月三日,阵面上擒得扑子蛮拷问之,并不语,截其腕亦不声……”由此可见西南边患日益深重,自然蛮汉战争会引起一些晚唐诗人的注意而成为边塞诗的新题材。如雍陶《哀蜀人为南蛮俘虏五章》,将视点集中于蛮军夺掠汉家人口、蜀地边民大批沦为蛮人俘虏的现实,着重表现西南边防之脆弱与边塞人民之痛苦。“但见龙城还汉将,岂知佳丽属蛮兵”“此中剩寄思乡泪,南去应无水北流”“越骗城南无汉地,伤心从此便为蛮。冤声一恸悲风起,云暗青天日下山”……这些诗成为西南边地战乱生活的一组剪影,曲折寄托了诗人对朝廷无能的失望与悲凉。另外,马戴诗《蛮家》却从另一个侧面表现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异域风情:“领得卖珠钱,还归铜柱边。看儿调小象,打鼓放新船。醉后眠神树,耕时语瘴烟。又逢衰蹇老,相问莫知年”,在我们面前真实地展现出一幅“蛮民”风俗画。如此直观地表现“蛮民”生活、把边塞主题从西北大漠移到西南“蛮地”,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唐代边塞诗的充实与突破。
总之,边塞诗的主题发展,走过了从初、盛唐的颂战、尚战,中唐的怨战、厌战而至晚唐的休战、反战的全过程,其格调也由盛唐的明朗壮大、中唐的哀婉幽怨而变为晚唐的凄厉和沉痛。
二
晚唐边塞诗作为盛唐、中唐边塞诗的返照和余响,其艺术成就和文学地位是明显不能和盛、中唐相提并论的。但作为边塞诗发展的一个阶段,我们也不能以忽略不计而简单待之。我们正可以分析它衰落的原因而总览唐代边塞诗完整的发展轨迹,以消除人们觉得它有始无终的困惑。
边塞诗在晚唐的衰落首先是江河日下的时代环境使然。唐王朝自从“安史之乱”遭受致命打击以后,在贞元、元和时期还保持过一段较长的“中兴”势头,这自然还能勾起中唐士人从军报国的边塞情结,引起边塞诗创作热情的高涨。如李益,清人沈德潜说:“从军十八载,五在兵间,故其为文,咸多军旅之思”,明人故应麟也说:“李君虞益生长西凉,负才尚气。流落戎旃,坎坷世故。所作之诗,悲壮怨转,乐人谱入声歌,至今颂之,令人凄断”。在贞元间他辑从军诗五十首,赠给友人卢景亮,可见其对边塞诗的倾心。然而时至晚唐,国势之溃乱一发不可收拾。长庆年间,河北三镇乱事蜂起,不久,延续近四十年的牛李党争又正式开锣,宦官专权发展到弑杀和擅自废立皇帝的严重程度……。晚唐前期,统治者还能倾全力对付内乱,如文宗谋诛宦官的“甘露之变”、武宗时期武力征讨昭义镇等,但后期却完全失去了反抗的力量,整个时局任凭宦官、军阀为所欲为,呈现出一派王朝末分崩离析、摇摇欲坠的景象。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文人士子再难焕发从军塞外、建功立业的豪情,正如苏雪林《唐诗概论》里说的:“边塞诗是唐民族势力向外发展的结果”,随着晚唐王朝对外征伐的无力,边塞诗也就失去了赖以产生的现实土壤。正因为如此,才使晚唐边塞诗显得零散而不成规模,一些比较集中之作均产生于宣宗大中年间和懿宗成通年间国势尚未完全糜烂之时。唐末光化年间的曹松凭他的边游经历写过一些边塞诗,如《塞上行》、《塞上》、《边上送友人归宁》、《己亥岁》等,虽成就较高,但毕竟难与盛唐高岑、中唐李益相比肩,只能成为绝唱而为唐代边塞诗作最后的加冕。再次,晚唐边塞诗的衰落也是由文学自身发展的趋势造成的。由于王朝日渐土崩瓦解,唐代士人心中的希望之火逐渐泯灭,整个诗坛的主流风尚由盛唐时期的抒情志、中唐时期的感事写意,回落到晚唐时期的体物缘情,着力追求形式的柔美纤丽和格调的婉媚怪诞。温李之风盛行,一改盛、中唐风骨兴寄、昂扬壮大的传统。“李义山诗,字字锻炼,用事婉约”,温庭筠“五、七言古,声调婉媚,尽入诗余”;贾岛受到推祟,李洞呼之为仙,孙晟画像朝拜……整个诗坛几乎没有给忧国忧民的边塞诗留下任何空间,这就使它只能在爱情、怀古、咏史、咏物等题材的夹缝中作为盛、中唐的余音而存在,在崇尚朦胧软媚、艰涩怪诞的审美氛围中日渐隐去它最后的余晖。另外,边塞诗在盛、中唐无论是题材主题、风格特点还是艺术技巧都已发挥到近乎完美的程度,使晚唐诗人再难超越,这也是晚唐边塞诗衰落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总之,正如陈伯海先生所说:“到晚唐理想破灭,主客观彻底分离,主观才真正忽视客观,转向自我封闭”国,在这种时代精神和封闭心态下,边塞诗在晚唐衰落和沉寂实在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必然。
总之,如果我们把边塞诗在盛唐比作中天丽日,在中唐比为午后斜阳,那在晚唐它就是一抹绚丽的余晖。它给唐代边塞诗划上一个完整的句号,同时也为后代文学埋下了种子。